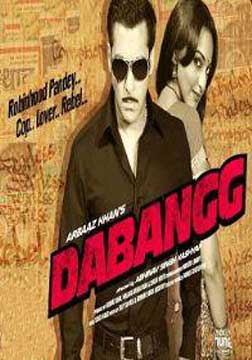电影明星,是那个年代被奉为最佳男、女主角的男神和女神,无论在电影中还是现实里,他们传递的精神气质,历来都与其所处时代的审美习性息息相关:他们既体现着当时社会对于美的认知趣味,又在很大程度上助推着这种潮流。“追星”“偶像”的本质无非如此。
就像八十年代,许多读者争相抢购《大众电影》,除了一飨当时紧缺的精神饥荒,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多瞅几眼封面女郎,参考她们的衣着样式甚至头发造型——在那个年月,拿着《大众电影》封面让理发师照着做发型的女顾客,并不在少数。
由是反观32届百花奖的历任最佳男女主角,几乎人人都曾被疯狂膜拜,而从这32届百花奖及其最佳男女主角身上,更是能抽离出建国66年来,中国社会审美潮流的嬗变历程。
1962年5月22日,北京政协礼堂,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里举行。崔嵬(《红旗谱》)和祝希娟(《红色娘子军》),荣膺首届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连做奖杯的铜都没有,两位当时的男神、女神,只分别获得了一个纪念奖牌,之后还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与群众联欢—其狂欢程度,不亚于周杰伦在演唱会上歌迷们的山呼海啸。1963年的第二届百花奖,依然如此。
崔嵬(《红旗谱》)和祝希娟(《红色娘子军》),荣膺首届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
在《红旗谱》里,崔嵬所扮演的农民想要翻身做主人,毅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的选择,凸显了特殊年代要求人们一心向革命的社会理念。再如《红色娘子军》里的祝希娟,她扮演的吴琼花,几乎浓缩了整个旧社会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而当她拿起枪去反抗并最终取得胜利,几乎释放了一代人的辛酸与苦痛。还有《李双双》里的张瑞芳,在集体主义面前“大义灭亲”,堪称大时代的道德楷模。
这是那个时代里,人们对男神和女神的选择标准:他/她必须是坚强、革命的,因而也是单纯、质朴的,他/她的气质必须契合新中国的新气象,贴合了大时代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旨。与之相应,且囿于物质基础的限制,人物的衣着外貌也呈现出朴素的样式。比如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发式是干练的马尾,上衣是淡红的格子纹,裤子耐脏耐磨,脸蛋还红润亮堂(这与当下女演员以白为美形成了强烈反差),充分体现了农民的本色。
在革命化的审美要求面前,性别差异的缩小,成了该阶段对女神的隐性衡量标准。该阶段对女性的审美,几乎剔除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就像《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除去尚未及肩的长发,她穿军装戴军帽扛军枪的飒爽英姿,几乎覆盖了一个女性几乎所有的生理特征,尤其她坚毅的目光,甚至成了那个时代里,女性也要且能战天斗地的无声宣言。
不同的时代,会造就不同的男/女神形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与困苦,需要人们“忆苦思甜”,需要人们追寻新时期的英雄形象,而且他/她们最好就在身边。
建国后十七年,中国电影的创作可以用“忆苦—迎新”概括:在新时代的基础上,电影对旧社会有了更充分的揭露理由,更能促进人们积极融入到新社会的建设中去,而这个过程,则带有明显的革命浪漫主义倾向:从《白毛女》《龙须沟》到崔嵬的《红旗谱》,即便是现在的观众,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真诚的欢欣之情。
1962年,文化部评选出了“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
应该说,那个时代中国电影里的英雄形象,远超当下漫威宇宙里的英雄人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他们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挣脱黑暗世界、为他人幸福生活的建立、为驱逐外来入侵之敌抛家弃业,英勇捐躯,昂然屹立在中国的银幕之上。他们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系列,除了《红旗谱》里的崔嵬、《李双双》里的张瑞芳,还有顽皮少年张嘎(《小兵张嘎》)、执拗青年董存瑞(《董存瑞》)、知识分子林道静(《青春之歌》)、正义律师施洋(《风暴》)、音乐战士聂耳(《聂耳》)、游击队长李向阳(《铁道游击队》)等等。
这样的时代背景与环境,注定要诞生像崔嵬、张良、张瑞芳和祝希娟这样的表演艺术家——与其说这些艺术形象是人民大众不自觉的审美选择,不如说他们是时代与环境的美学造就。这就像那个时代里的服饰,诸如粗布衣、中山装和工装背带裤,以及受前苏联影响而来的列宁装和布拉吉长裙等,它们既贴合了当时物质紧缺的现状,又迎合了要建设新中国的社会需求。而“大众电影百花奖”选出来的男神和女神,更是当时社会审美的高度体现,无论是其在现实生活里透出的高贵艺术品质,还是他们对人民群众的亲切,都经电影的英雄主义情怀投射后,散射出浪漫主义的光芒。
“文革”结束后,“百花奖”恢复了最佳男女演员的评选。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折射到中国电影和社会审美里,就是人事物多元化的呈现:既有对“文革”伤痕的反思,也有对以往电影传统的回溯,还有对中国电影新方向的探索——尽管路数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电影人的自觉审美追求。
李仁堂、达式常和杨在葆三位艺术家,分别在1980、1981和1984年荣膺“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李仁堂在《泪痕》里扮演新任县委书记朱克实,走马上任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除了十年动乱后依然残留在政府内部的偏执余孽,既为在动乱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人讨回了公道,又带领该县重新恢复经济生产,成了人民心中的大救星。杨在葆的《血,总是热的》跟《泪痕》异曲同工,都用新任领导高大刚正的形象,感动了亿万观众。相对而言,达式常在《燕归来》里的表现,更多是对动乱期间遭受迫害的人的泪点宣泄,而他之所以将林汉华这个角色拿捏得如此精准,跟他本人在此期间的遭遇不无关系。
在《血,总是热的》中,杨在葆发挥自身优势,依据人物心理性格及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把厂长罗心刚那种大刀阔斧、处乱不惊的气度表现得恰到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堂和杨在葆的角色,虽然建立在文革的背景之上,但他们所传递的审美意象,其实与“文革”之前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并无二致:他们依旧浓眉大眼、目光果敢、脊梁笔直,义正言辞时能在地上砸个坑,抬步行走时手臂旁呼呼生风——对“文革”前电影回溯的尝试,依旧没能摆脱这个路子。从这层角度看,当时社会对“男神”的审美要求,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电影模式的窠臼,人们潜意识里并没有彻底摆脱旧式的英雄浪漫主义。翻看最佳男主角名单,王新刚、吕晓禾、古月、李雪健、王铁成、李保田和高明等艺术家,该阶段塑造的角色光辉,依然保留着“浪漫化的英雄美学”色彩。
凭借对阿Q的演绎,严顺开获得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二届瑞士国际喜剧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获得“卓别林金拐杖奖”的演员。
但令人欣喜的是,“男神”的队列里挤进了文学史上的“丑角”阿Q(严顺开),《芙蓉镇》里绵里藏针隐忍存活的秦书田(姜文),和被社会的传统纲常压制到苦不堪言的孙旺泉(张艺谋)——百花奖将这些角色奉为“男神”,不仅是它与时俱进的佐证,更是大众对男性审美的幡然醒悟:男人是否一定刚健强硬?是否永远光明磊落?脆弱、柔软和隐忍,难道也要分性别而待之?百花奖对这些男主的选择,正是将本性归还给人的开始——这既是百花奖的进步,更是社会审美开始艺术自觉的表征。
张瑜在《庐山恋》里带来了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个吻,而正是这轻轻的一个吻,开启了中国电影正视男女身体之美的先河。
当电影艺术把本性还给人,最先得到解放、也最早呈现多彩姿态的,其实是女性。1980年,张瑜在《庐山恋》里饰演女一号周筠,带来了新中国银幕上的第一个吻,而正是这轻轻的一个吻,开启了中国电影正视男女身体之美的先河。而且,在这部电影里,张瑜共换了43套服装,远远超过《花样年华》里张曼玉的23套旗袍,而张瑜也凭借这部电影,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观众心目中的“梦中情人”。此后宋佳、宁静和郭柯宇对身体的部分裸露,都不过是对这口香吻的身体性延伸。
《股疯》中的潘虹。
当然,除了这种突破,更多女性形象还是将身体与身份的美,克制在家庭和职场的情境里,如陈冲、徐秀明、吴玉芳、方舒、斯琴高娃等,角色形象的呈现属于“浪漫化的英雄美学”时期,但她们的成长,却剔除了《红色娘子军》里被强化的男性特质,显出了更女性本色的轨迹。相对而言,潘虹、刘欣、刘晓庆和刘蓓在这个时段的女神气质,则更多给人以柔中带刚之美。
杨在葆的高大刚健、严顺开的胆小怯懦、张瑜的风情万种……这些不同形态的人物气质,构成了多元化的角色美,也折射了那个年代的审美,变得更“接地气”。也就是说,百花奖选出的这些男神女神,是观众审美趣味发生改变的表征,暗示了人们不再把宏大的历史命题放在首位,而是开始关注与自己相同的、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尽管这些体验多半仍以大时代为背景,但它毕竟是个人化且多角度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审美意识革故鼎新的开始,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审美倾向的位移,其核心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人生态度,以及确认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表现在银幕上就是人物形象的多元化。
1993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荣膺百花奖最佳女主角,而前一年,巩俐刚凭《秋菊打官司》,成为首位获得威尼斯影后的华语女演员——也就是说,在全民审美多元化时期,中国社会对女神,尤其是对电影的认知,已然与国际接轨。
一个时代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1998年,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冯小刚拍摄了贺岁片《甲方乙方》,在这部电影中,葛优和刘蓓的穿着打扮极具时代的特征。葛优性格随性,服饰呈现出了休闲随性的样式,而且都以西式服装为主,夹克、休闲长裤占据主导地位。而刘蓓的角色是一个职业女性,所以我们能看到她一直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银幕上。这表现了在新的时代里,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升,而男性则从传统的“主要劳动力”变成了“次要劳动力”。
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这个时代里最新的变化。而女性的地位提高,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之后,还出现了另一个审美的现象,那就是女性的喜好,成为了主导市场的工具,女性的喜怒哀乐、价值趣味变成了市场上的中流砥柱。
如此一来,男性的形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白脸、娘娘腔,这种在几十年之前倍受唾弃的形象再次崛起,孔武有力的男子汉,以及略有“直男癌”倾向的人物,都被甩到了时代的身后。换而言之,在这个时代里,唐吉可德式的人物失去了市场,而哈姆雷特那样的优柔寡断,思前想后、担心责任的人物成为了主流。葛优在《手机》里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徒有其表的文化人,处处留情又不想承担责任。
而阴柔之美,也在这个时代开始流行,《画皮》中的陈坤、《失恋33天》中的文章,都是阴柔美的代表性人物。娘娘腔不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女性最爱的男闺蜜。男女关系也由授受不亲转移到了乐意互相分享秘密的亲密朋友。这样的变化,与其说是女性的需求,不如说是社会对男性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劳动力、捕食者,变成了心灵的倾诉对象和分享秘密的伙伴。劳动,体能和责任感不再是社会与女性对男性的唯一诉求,所以女性即是社会审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代表者,又是社会审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享有人。
阴柔形象的盛行,并不意味着阳刚之美就乏人问津,《硬汉》里的老三刘烨就是阳刚形象的个中代表,这种憨萌的肌肉男,亦对之前高仓健为首的男子汉形象进行了改写。而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坐在冷板凳上的“书呆子”了。《中国合伙人》中,三个好哥们一起开办了英文补习学校,为了理想——同时也是为了钱——努力和拼搏,动用了各种脑筋,最终成功上市,成为了新时代里的“文化商人”。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归功于制度和社会的变化,归功于人们对金钱态度的转变。虽然都是“在北京”,但是黄晓明和张国立(《混在北京》)的“混法”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开始变得愈发国际化,乡村与家庭属性,都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以至于女性形象开始迅速和国际接轨。那些可以用身体上位的蛇蝎美女的形象(范冰冰《手机》),具有正义感和道德力量的反面角色(刘若英《天下无贼》),身负家国仇恨完成男性使命的人物(章子怡《一代宗师》),在不同男人间难以抉择的女人(徐静蕾《开往春天的地铁》)以及一位失恋把自己逼到绝境变成“外贸尾单货”的小可怜形象(白百何《失恋33天》)都出现在了银幕之上。
对比几十年前,银幕上的女性还在断文识字,为自己的权益拼死相争,这十几年来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是巨大的——这种幅度从布拉吉连衣裙开始,一直延伸到职业装和范冰冰身上的高级成衣;从灰蓝色到色彩斑斓;从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到薄露透短——银幕上的女性和现实中的女性一起,走出了一条通往国际的道路。
百花帝后汇聚“百花之夜”
2015年9月18日,“大众电影•百花之夜——向中国电影人致敬典礼”将在吉林省吉林市第24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隆重举行。
祝希娟、张良、牛犇、斯琴高娃、吕丽萍、孙海英、王馥荔、李雪健、王铁成、卢奇、高明、阎青妤、吴军、邓家佳、张光北、张涵予、赵薇等近20位历届百花奖获奖演员将齐聚“百花之夜”。
在“大众电影•百花之夜——向中国电影人致敬典礼”中,将通过视频短片的方式回顾《大众电影》创刊及“百花奖”诞生,揭开1950-60年代的电影记忆。届时首位百花影后祝希娟登台演讲,倾情讲述与电影、与百花奖、与《大众电影》结缘的故事。
在“百花·记忆”环节,邀请获奖演员代表祝希娟、张良、王铁成、牛犇、杨在葆等共同回忆百花奖获奖故事。在“百花·鉴证”环节,李雪健、斯琴高娃、宋春丽、吕丽萍、王馥荔等艺术家重温经典电影桥段,赏鉴中生代表演艺术家们的演技与风采。在典礼的“百花·怒放”环节,将回顾《大众电影》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及“百花奖”的转型。90年代以后“百花奖”获奖演员代表在舞台上以微演讲形式讲述独属于自己的电影梦并展望中国电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