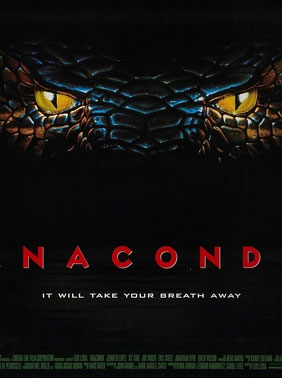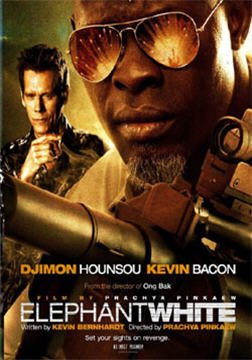我是路人甲,一天我和路人乙在马路中间走。突然一辆大卡车撞过来,我们都成了路人饼。
——社长说
文/高成新、刘洁
本文系原创,转载请联系微信号:isocialor
最近上映的暑期档电影一部接着一部,《我是路人甲》(7月2日上映)、《道士下山》(7月3日上映)、《大圣归来》(7月10日上映)、《捉妖记》(7月16日上映)和《煎饼侠》(7月17日上映),都成为了我们谈论与刷屏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电影带给我们的社会学想象。
我是路人甲
社会分层的起点
《我是路人甲》记叙了“横漂”一族的追梦故事,讲的很接地气。电影中,有些情节很励志,比如曾当过煤矿工人的覃培军,正能量满满的励志哥,喊出“你不努力,怎么会有结果”;也有些情节很现实(现实到有些灰色),比如对做群演感到心灰意懒的王婷,已经决定离开横店、重新打算未来,对刚来的横漂说“新来的总以为自己能怎样怎样,大部分都是失望”;还有些情节很温情,比如因为爱情,那些面临物质等阻碍的人们还是最终走到了一起。
故事的主人公万国鹏最初对自己的“横漂”身份很乐观,认为虽没有“二代”背景,但是凭借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就能够闯出一片天。在横店,他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做群演,但最后给自己的定义却是“没当上演员的演员”。相对的,张冠仁则在《如你我一般浮沉的小人物》一文中写道,“我所接触的大部分群众演员……很多人只是和工厂流水线两相比较后,认为群演更轻松。他们像候鸟一样,随供求关系的稀缺变化在流水线和影视基地来回迁徙。”
怀揣演员梦的横漂,大概在漂了一段时间后都要重新审视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原因就如片中所言:出身中戏北影的人进组就能当主演,而横漂则要自问“你见过谁最终混出来了”。——这便引出了社会分层的必要之所在。
戴维斯和摩尔认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对特定社会位置的奖赏(如物质报酬和社会声望)是根据这一地位的重要性与适配人员的稀缺程度来分配的。毋庸置疑,出身科班与横漂一族从一开始就被分配到了不同资源的入口处;因而我们说,起点就是资格:中戏北影的学生身份就等同于演员的角色,这是横漂们单纯凭借“梦想”和“努力”很难跨越的,此现象与“文凭主义”“名校情结”有着一样的逻辑。
不论演员还是其他,资历是在信息不能充分展示的情况下,交换双方节约沟通成本的有效要素。影片中的横漂希望有机会去参加北影的培训班,他们都知道那不仅意味着能够学习到更多的表演技巧,更象征着可以见到大导演、并可能被选为演员。也就是说,与“北影”有关的资历被看作是得到更大机会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电影中横漂有几次都将自己的境遇与“二代”的成功进行对比,既有无奈,亦怀不甘。这里牵涉到的“阶层固化”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它意味着社会流动的放缓甚至停滞、社会阶层的复制或曰循环、以及权利与机会分配的定型和垄断。
不能否认,在资源尚不能绝对公平分配的前提下,个体天然的先赋地位将对后天的自致地位施加影响,这与布迪厄指出的文化资本会在代际间传承、从而实现阶级再生产的机制是一致的;而“二代”的出现,更是意味着在家本位的文化传统中,先赋地位成为了个体的主要身份,这时如果个体在不同身份团体中比较“奋斗”的意义,常常会感到“很受伤”。但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并不可取,该怎么做?电影《道士下山》给出了我们答案。
道士下山
社会化是学“器”,更要习“道”
《道士下山》讲述了小道士何安下在动荡纷扰的尘世间的历练故事。未得开化的何安下在下山后,先后遇到了药铺老板崔道宁与其妻玉珍其弟道融、武功高强的扫地僧周西宇和其师兄彭乾吾其师侄赵心川其世侄彭七子及其挚友查老板,还有得道高僧如松长老、彼此爱慕的王香凝等人。每每在一句“师傅收我做徒弟吧,把本事交给我”的启幕之后,何安下便在爱恨恩怨中卷入是非情仇,感受践行着下山前师傅的那句叮嘱“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何安下的成长经历,其实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与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体验。电影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社会化既包括习得技能、掌握规范等“器”的一面,也涵纳完善人格、寻找自我的“道”的一面。就如同叶匡政指出的那样,“《道士下山》表面是一部武侠片,它想展示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心的文化。像小道士的名字一样,追问的是如何安下自己的心。”
我们在基本社会化、继续社会化甚至再社会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充实知识、丰富经验,更是要在精神层面充盈内心、不负良知。这后一点似乎与提倡实证精神、主张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旨趣并不相容,但是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命题,即社会单位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费老指出“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基因,任何文化都是一颗种子”。
《道士下山》对儒释道的核心价值进行了展示,社会化研究也更应在关注“谋食”的同时,思考如何开展对“谋道”的体悟。而言及传统文化,便不能不提好评如潮的动画片《大圣归来》与奇幻片《捉妖记》。
大圣归来、捉妖记
情感与理性的对决
《大圣归来》的英文名是Hero is Back,讲述了虽在被压五百年后恢复自由身、但却依然被禁锢法力的孙悟空,在护送解除其封印的小和尚江流儿回长安城途中,相互陪伴、勇斗妖王、终于找回真正自我的故事。可以说,孙大圣的回归最契合我们赋予“成长”的英雄色彩:历经磨难、也曾落魄,但是因缘际会、不忘初心,终于让你等到看到了“我”归来的样子。
《捉妖记》取材自《聊斋志异》中的《宅妖》,背景设定为在人妖划界而治的年代,妖界和以捉妖为己任的天师界都希望能捉拿到老妖王的孩子小妖王,永宁村的保长宋天荫则意外地被牵涉进这场纠纷中(妖后将怀着小妖王的蛋塞到了天荫嘴里,成为“孕夫”的他只能选择将小妖王生出来)。之后,为了能够卖掉小妖王、换取重金奖赏,捉妖天师霍小岚拉着宋天荫一路养育保护小妖王胡巴。然而在将小胡巴卖掉后,终是因为舍不得,霍小岚又与宋天荫一道救好妖、斗坏妖,最终,各得其所、圆满结局。
两部电影的主题,都离不开“感情”这一要素。我们知道,在对讲求得失计算的理性化研究投入了诸多精力后,一些社会学家将目光转向事实的另一面,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了情感社会学,王鹏和侯钧生便将情感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分为情感的社会根源、情感的社会化以及情感的社会后果等三个方面(《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在《大圣归来》和《捉妖记》中,既存在完成任务的工具性关系,也有着表达心绪的情感性关系,但最终一味实现目的的工具关系都没有敌过让人动容心暖的情感关系,邪恶被打倒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情感体验、有情感能力,也能提供情感支持。
情感会战胜理性的冰冷,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拉近彼此距离。《大圣归来》里当江流儿说“我要向佛祖祷告,恢复大圣的法力”时,那个遍历冷热悲欣的落拓英雄,何曾不受到感动?而《捉妖记》中当反被一直要捉拿的二妖竹高与胖莹救下后,若没有情,捉妖天师罗钢又缘何与他们成为了并肩作战的朋友?
进而,情感也会成为连结、拯救、赋予勇气、激发生命力的一剂良方。一遍遍说着“我管不了”的大圣,最终被“别忘了,你是大圣”“齐天大圣是不会死的”的需要所点燃唤醒,完成了自我的救赎;而当卖了胡巴却看到ta留下的、一块用牙齿咬出的天荫、小岚和胡巴一家三口的图画后,只打算卖妖换钱的捉妖天师小岚,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二话不说、赶回去挽救小妖王。——这,无疑都是出于情感的支持力,而非理智的客观权衡。
煎饼侠
从标签消费看人言可畏
《煎饼侠》续接《屌丝男士》的故事,吸引众多大咖加盟,拯救不开心:原本如日中天的演员大鹏因被陷丑闻而跌入谷底,经济、人气和人脉都惨遭“人走茶凉”。但之前签下的拍一部“全明星阵容”的电影协议又不能不继续履行,于是大鹏想到了用偷拍明星的方法来低成本、高规格地完成电影《煎饼侠》——所以,我们看到的《煎饼侠》是在讲述大鹏和朋友们如何拍出《煎饼侠》这部电影的搞笑故事,是谓“戏中戏”。虽然电影完成了逗笑观众的喜剧道德,但其中并不乏戳中泪点之处。这里仅举一例。
《煎饼侠》还没拍完,落魄的大鹏有幸被另一家公司所接纳,这时他要放弃还未完成的《煎饼侠》而继续出演屌丝。心有戚戚的大鹏便和柳岩在天台上进行了一段对话,柳岩有些哽咽地笑说“这么多年,别人就会说,柳岩什么都不会,就只会借胸上位。”就这一句,不悲情不滥情、不怨天不尤人,笑中带泪、自嘲自黑,听闻后突然就控制不住地落了泪。再联系电影中柳岩还说过的“衣服穿得少一点,日子过得好一点”、大鹏那句“我不想再演屌丝啦”,以及袁姗姗之前在Tedx演讲中提到的“2013年的夏天……袁姗姗这个名字好像从此和‘一无是处’划上了等号,那个时候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演什么都不对”——一句一句,都向我们指出了“标签消费”的粗暴与蛮横。
杨时旸写道,“在这个网络时代,作践自己有时是唯一能成功的捷径,这真残酷,但他们作践的时间长了,观众就分不清角色和演员,他们就被角色附体。”在快节奏的社会,我们似乎缺乏着去认真了解一个人的耐心与精力,于是给事物贴上一个碎片式的标签,既简化认知,又便于沟通。但是这种定型化的评价,束缚了被定义个体展示多元真实自我的可能,尤其是当它演化到污名、刻板时,就会引发一场场的网络欺凌。
人言可畏,这个“畏”,不应当是“畏惧”,而应该是“敬畏”。只有当我们对评价与言说的权力保持审慎的自觉,才能让语言具有真诚、真理、正当的沟通理性,才能塑造出平和、多态、健康的对话空间。
总而言之,电影的吸引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浓缩、集中地呈现了一幕幕对主人公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生命事件,让我们在例行化的日常生活中,嘻嘻哈哈、呜呜呼呼,在共鸣与移情中,将最纯粹的自我,肆意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