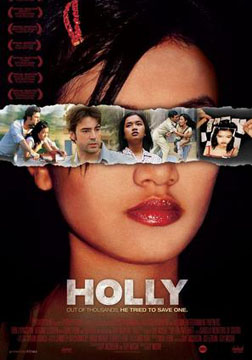世事就像一根拉紧的皮筋,随时有崩坏的可能,这种电影带来的不安倒是和小丰、杨自道和陈比觉那七年负罪卑微地活着的心境吻合。
莽莽人生,我们都是逃亡者。

是在一个月前看的《烈日灼心》,当时要为不久后邓超的专访提前做功课。开演前,提前看了一段花絮纪录片,讲的是【注射】那一场,邓超四肢被捆在一张黑色的床上动弹不得,嘴唇苍白,针管插进胳膊里,他胸脯剧烈的起伏,然后渐渐没了知觉……旁白里,他说那一场,他们选择了真实的注射,他感觉自己停不下来的痉挛和抽搐,“我的光慢慢没了”,然后他听见有人哭,导演喊了停,这个人还是停不下来的大声哭,是他的执行导演,“他说超哥我以为你死了。”

当时我以为那是一场逼迫他承认罪行的惩罚,电影到尾声才知道,那是死刑的行刑现场。于之前七年的逃亡和隐匿而言,这一场对他们罪恶的审判和死亡的宣告来得太快了,几乎是潦草而鲁莽的。以致于我始终无法对电影的结局感到信服。创作者就像生怕观众不知道他们杀了人跑了路一样,掰开了揉碎了,一刀一刀戳着他们脸上的面具,戳得深一脚浅一脚。段奕宏和郭涛在医院里重遇那一场,两个人的眼神特写都呈现得太过露骨了,让人不得不皱紧眉头狠狠心疼起这几个亡命天涯的人,根本不想管什么人性善恶黑白之类的事情了,因此失去某种自由判断和感受的能力。影片后三分之二更是进行得堪称快速、简易。另一只鞋掉下来了,“像一把风吹发断的快刀”。
印象里,只有一次感觉内心极度挣扎矛盾和难受的时刻,就是在高楼顶层追击时,邓超紧紧抓着段奕宏的手,他只要一松开,这位知道他秘密的警官先生就会立马毙命,松,还是不松?几乎有一刻,我觉得他(邓超)就要“得救”了。然后心里又马上升腾起另外一个声音,即段奕宏又做错了什么……那场戏看得我心里恐惧异常,一半是为那样惊险的场面,一半是为自己内心的那处阴暗的存在。
而这份对自我原罪的焦虑,就在不久之后被邓超以一句台词“治愈”了。就在那栋他救下了段奕宏的高楼顶层,等着他的是一双手铐。段奕宏问他:“你恨我吗?”他憋了很久很久,说感谢他,一切痛苦终于结束了。
邓超、郭涛和高虎,三个人,就这么替黑暗里无辜或负罪观众们,受了苦,受了难。
其他线索上的人物禁不起细想,每一个都令人感伤和不解。
王珞丹想过救他们,也确实做了,却依然阻挡不了事情的发展,她爱上了一个“活死人”,她的爱一样真挚,却像石头扔进大海,在行刑那一场里,我们只看到她戴着大墨镜遮住半张脸,只能看到她鼻翼不动声色的颤动;
那个在高楼顶上因为挥舞斧头用力不当致使高空坠落的协警;
还有到结尾都下落不明的窃听者房东(他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在半山的坡路上和段奕宏擦身而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这个镜头里的他被处理得假装若无其事)。

谁就应该无辜地死吗,谁又凭什么苟且地活着。谁为什么不能随心地爱,却又那么轻易地恨。
一切让人觉得世事就像一根拉紧的皮筋,随时有崩坏的可能,这种电影带来的不安倒是和小丰、杨自道和陈比觉那七年负罪卑微地活着的心境吻合。
莽莽人生,我们都是逃亡者。
《烈日灼心》这样的词组里,“灼”是唯一的动词。查询词源才发现,除了我们以往了解的“烧”、“炙”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明白、透彻。也许是电影的另外一层含义,让人剥开混沌,见得某种残忍甚至难堪的真相。就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
《烈日灼心》之后,剩下的,只有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