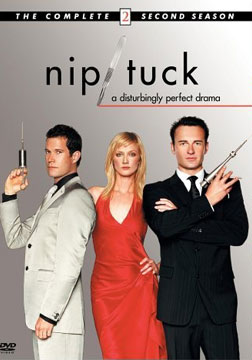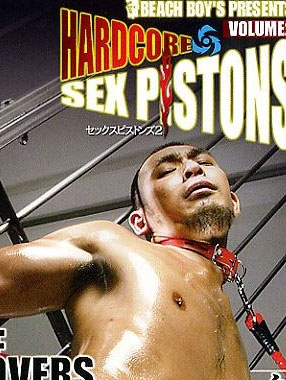鹤寿千岁,以极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尽其乐,盖其旦暮为期,远不过三日尔。

原本打算以一种煽情的方式来写这样一个命题:香港的户外广告牌即将被当作违章建筑而拆除。
戴上耳机,听着舒淇绵软的台湾腔广东话,从日薄西山坐到月影阑珊,却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Louis Vuitton Soundwalk——舒淇 慢行在香港

酝酿了许久的情绪,事与愿违般地越来越平静,到最后连一声感叹都显得矫情。说到底,我和香港并没有熟悉到能够伤春悲秋的地步,而广告牌的命运也并没有像被炸毁的巴尔夏明神庙那样震撼到足以牵动一个陌生人的心。
事实是,在一个千年遗址和工业园区处于同等危险当中、飞机和电梯享受同样事故概率的年代,为了历史不足一百年的商业副产品正经做一番文章,略有伪文艺之嫌。

煽情的路走不通。然而心里总有点惆怅,类似“取缔了赌场的维加斯”“刷白了屋顶的圣托里尼”“不允许奇装异服的原宿”“砍掉了时装周的巴黎”一样的惆怅。
鹤寿千年,并不一定觉得怎样珍惜某年夏天经过的荷塘;蜉蝣朝生暮死,极有可能对载着它渡过半生的荷花瓣念念不忘。我承认这也只是站在人类角度的推想。



继续推想下去,俨然已经成为地标的一样东西,哪怕是并不精美的广告牌,象征意义也早就超过了其本身的实用价值。真要说拆就拆了,记忆的某一块也随之被掰断扔掉,而空出来的位置再也没有什么填的上。
那些捕捉了生活在香港霓虹下的人物的内心世界

美都餐室
我们在这里度过休闲的时光,营业时间过后便在这里打麻将。我们的霓虹招牌就是我们的品牌。客人看见它,就会懂得怎么上店铺上层找我们。

英国露云毛冷巴黎公司
我们自1971年起便在这里,而我们的霓虹灯自那时起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招牌老了,没有人愿意修理。但我们仍然为它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和这个招牌一样在这公司工作了大半辈子。

亚洲红龙
也许这是街上最好的霓虹招牌,这个地方是我老板的,而我喜欢我看见外面的光

仁泰大押
这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夜生人静的时候,霓虹光点缀了这里。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很难从香港人的角度去想象没了广告牌的香港。但是我不知道拿起相机框不到层层叠叠的广告牌,我还能拍什么。


这很肤浅,不牵涉到王家卫、爱买杯子的旺角卡门、没有脚的鸟什么的。
除非能允许市民自由涂色,否则我们将要面对的会是毫无美感可言的外墙,类似不爱红装爱武装、姿色平平偏不化妆的半老徐娘。在这样的环境里,审美由精致退化到粗糙只是个时间问题。


审美有多重要?往小了讲那是可以扫天下之前收拾好自己屋子的条理和细致,往大了讲一个文明剔除糟粕留存精华靠的就是对好与坏的准确判断。
往往越繁盛的时代伴随着越高超的审美,比如古希腊和盛唐。那么反过来想想,恐怕惆怅的人只有更惆怅了。

几年前舒淇录制的时长一个钟的sound walk里,说起“香港的一秒等于纽约的一分钟。这城市不会慢慢的重修,而是把一切推倒后再重建。”当时听了不觉得怎样,现在却觉得也许变迁来得比预想的还要快很多。

“反正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照片。”也许还是存在虚拟空间的电子照片。那也没什么。只希望代替那个“白色燕子图案的蓝色霓虹招牌”的,是更美好的景象,而不是一片虚无。
如果你睡不着,就跟着舒淇去香港转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