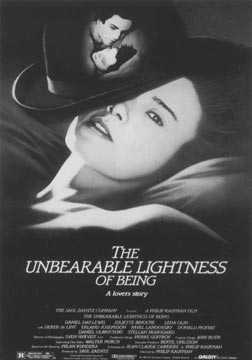最近在国内的大银幕上接连有几部国产警匪片上映,包括《烈日灼心》《宅女侦探桂香》《东北偏北》《解救吾先生》等。警匪片在中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不好拍,当这么多警匪片密集出现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专门关注下。
有城市的敌方就有犯罪,有犯罪就会有警察和罪犯的斗争,因此警匪片是一种全球化的城市犯罪电影,而好莱坞警匪片又对所有国家的警匪片都有深刻的影响,这里先介绍下好莱坞警匪片的历史。
警匪片在好莱坞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三十年代初期流行的黑帮片,一个是来自文学传统的侦探片,其中包括与黑色电影杂交的私家侦探片。真正以警察抓获歹徒为情节主体的警匪片出现得较晚,在之前的那些电影中,警察常常被描绘为无能、迟钝的饭桶形象,关键时刻毫无用处,甚至帮倒忙,只有案件告破后才出来收拾残局。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后开始改变,正面展现警察破案的电影开始涌现。这个时期的警匪片受到四十年代末期写实电影风格的影响,喜欢细致描写警察日常工作中那些平平无奇的细节,打个比方的话,略类似于中国导演宁瀛拍摄的《民警故事》。这类警匪片强调警察的责任、纪律和专业素质,警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精神和价值的守护者。

《警网铁金刚》
到了六十年代末,另一类和过去截然不同的警察形象开始在银幕上亮相,并且带出一波在影史上也非常了不起的警匪片。一方面是因为审查制度的废除,电影展现暴力的尺度大大拓宽,另一方面,越战的爆发让社会价值分裂,警察也不再拘于严谨奉公的呆板形象。《警网铁金刚》(Bullitt,1968)、《独行铁金刚》(Coogan’s Bluff,1968)、《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1971)、《肮脏的哈里》(Dirty Harry,1971)这些警匪片中的警察,以演员史蒂芬·麦奎因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角色为代表,强悍、暴力、独来独往,对待罪犯不择手段、绝不容情,他们在银幕上修复了在现实中失去民众信任的警察形象。
六、七十年代警匪片比起较早时候会更多地表现动作,这种趋势到八十年代就发展成警匪动作片(也受到兰博一类电影的影响),是那段时期的主流票房大片,比如布鲁斯·威利斯担纲的《虎胆龙威》、梅尔·吉布森领衔的《致命武器》等等。激烈的枪战和动作奇观场面成为警匪片的标准配置,不再讲究真实的破案流程。

《虎胆龙威》
从九十年代至今,好莱坞流行的警匪片风格又为之一变,观众看腻了肌肉男的对打,转而欣赏纯粹智力之间的对抗,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拥有高智商的罪犯开始变得比警察更有魅力,《沉默的羔羊》中的安东尼·霍普金斯,《七宗罪》中的凯文·斯派西莫不如此,让人联想起二十年代德国电影大师弗里茨·朗塑造的无所不能的马布斯博士。而警察也需要变得更加聪明和反应灵敏,依靠严密的逻辑和细致的观察来将罪犯绳之以法。
警匪片亦是香港电影中的一种主流类型,尤其是从八十年代以来,蔚为大观,代表作包括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无间道》三部曲等。香港警匪片受好莱坞警匪片很大影响,但植根香港,也发展出一些地方特色风格。作为中国观众,可能对香港警匪片的熟悉程度更在好莱坞之上。而且「警匪片」的命名很可能是来自香港,因为在英文中是说police procedural或者police crime drama,并不提到「匪」。

《沉默的羔羊》
中国内地拍警匪片的历史不算短,但因为掣肘因素颇多,我认为始终没有形成稳定和独特的风格脉络。在过去,我们更习惯用「公安片」而不是「警匪片」来给它命名。这个差异说小不小,「公安片」实际上指明了它属于行业题材的实质,过去有人把它更具体地分为反特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刑侦片等,是对公安工作性质的细分。犯罪分子在「公安片」里的地位是从属性的,是公安干警工作的对象和目标,它就不像警匪片那样更强调警匪双方的对抗。因为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公安片」又极易落入主旋律的范畴中,政治意味变得突出,这样对警察和罪犯的塑造就会显得非常单一。警察就是正义的化身,几乎不能有缺点,也不提倡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在罪犯这边,不可以写复杂人性和犯罪动机,同时对警察侦查手段也不可以有过多涉及,以免有同情罪犯和教唆犯罪的嫌疑。
观众多年来受到好莱坞和香港警匪片的熏陶,基本接受了相应的类型程式,对传统的公安片是比较排斥的,传统公安片的创作思路也不太能适应市场化警匪片的要求,因此内地警匪片面临一个重新学习和开拓的过程。

《无间道》
本文开头提到的几部新的警匪片,也都在不同层面有一些可喜的小小进步,《烈日灼心》表现了在中国电影里前所未有的一种警匪关系,而《解救吾先生》则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恶人形象,不像有的俗套电影那样以为让坏人带上点善,似乎就等于有了丰富的性格层面。并非如此,王千源在《解救吾先生》中演的绑匪恶到了极致,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善,但他的邪恶光谱却是立体和善变的,因为恶远非只有一种。
警匪片不会是电影市场上最卖座的类型,喜剧片、幻想片、动作片都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但我非常期待中国警匪类型的发展,比较现实地说,它标示了当前创作在某些方面的边界,也为刻画那些我们在中国电影中从未见证过的复杂人性提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