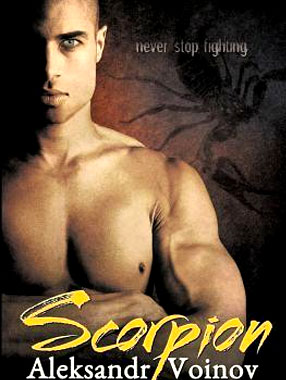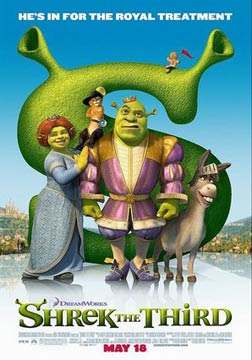侯孝贤戛纳获最佳导演奖肯定是本年度台湾电影最重磅的一个事件。凑巧的是,侯导带着《刺客聂隐娘》出征戛纳的时候,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台湾闲逛。
初到台北的那晚,我们最想做的就是看场电影作为融入这个城市的第一步。翻开长长的影讯从头到尾,台湾本土电影除了以日本AV女优波多野结衣为噱头的《沙西米》,同志形婚的家庭喜剧《满月酒》,就是已经在大陆影院看过的《念念》,仅此三部而已。
如此少的选择让我们无从下手,最终弃台片而看美国电影。接下来在台湾的一周时间里,我和朋友一直不断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忽然之间,有着如此优良传统的台湾电影会衰落到如此地步?它的「疲软」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

《念念》
比起八十年代「台湾新电影」涌现出的这一批电影人才和他们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青少年哪吒》《戏梦人生》,这些年的台湾电影代表作《海角七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艋舺》《塞德克·巴莱》之类,分量无疑轻了几个段位。
尽管魏德圣师从杨德昌,钮承泽由侯孝贤带入电影行业,但这些后继者却似乎将他们「师傅」的视野、情感和思想价值完全抛到了脑后,仅仅满足于作品在华语电影圈内的商业口碑效应,而将电影的核心艺术价值拱手出让。
以钮承泽去年颇受关注的《军中乐园》为例,它的题材在华语电影中绝无仅有颇有挑战性,又由侯孝贤督阵剪辑,影片的水准似乎没有道理不跃上几个台阶。但成片的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创作者仅仅停留在题材和人物的最浅层表面:只有轻佻、煽情和故作姿态,却没有态度、重量和足以撼动人心的冲击力。因为缺乏核心的主导价值,影片开始不久就浮于表面散成了一盘沙,随之溃堤千里。而此片在台湾业内人士的眼中,已然是2014年的最高水准。

《青少年哪吒》
《军中乐园》让我们意识到台湾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商业抢夺了艺术的阵地,而更是电影创作者本身缺乏深入题材与人物的视野的能力,丧失了树立影片核心思想价值观念的意识。
对于所叙述的主题缺乏深入的认识而流于表面的致命缺憾不仅仅是新一代台湾导演的顽疾,甚至也传染到了老一代电影人身上:十年未执导筒的张艾嘉返回台湾拍摄的《念念》本应是今年台湾电影最让人期待之作,但一个以骨肉分离寻亲之痛而透视血脉亲情的伦理剧,被带着文艺腔的凄风苦雨口吻叙述的毫无节制,对催泪效应的关注远远高于对影片核心意图的展现。
《军中乐园》和《念念》差强人意的表现让台湾电影幼稚而浅白的通病暴露无疑,但就在这时从戛纳传来了侯孝贤勇夺最佳导演的消息:《刺客聂隐娘》不但成为了台湾电影最新闪耀的光环,同时也提示我们两代台湾电影人之间的本质差别:

《军中乐园》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在侯孝贤张扬的个性和爆棚的自信心后面,他有着一颗极为敏感细腻而趋向「谦逊」的内心,他关注的是那些所散发出活力与魅力的人物,冷静地呈现他们深陷世俗世界中无法逃脱的苍凉宿命。
此外,侯孝贤有着极其成熟的社会、政治和历史价值观:无论是《悲情城市》的宏大冷峻视角,还是《戏梦人生》通过个人命运对台湾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描述,无不是他坚实而深入的个人价值观念表达。
在对影片内在情感和思想价值的反复分析、衡量和取舍基础上,侯孝贤以出人意表的镜头调度设计和自然主义化的演员表演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语言风格,他的影片不仅是感性感受的情感内容,更是理性表达的成熟形式。

《戏梦人生》
正像他曾经在纪录片《侯孝贤画像》中所说,宏观上的中国式思维耳濡目染地赋予了他最基本的感性和理性价值取向,这是《海上花》《刺客聂隐娘》这类蜚声国际影坛的作品的创作起点。有了这样多元的个人素质和电影创作素质,华语电影才有幸拥有了一位侯孝贤。
当我们比较侯导和新一代台湾电影人,不难发现的是,成就前者臻于大师境界的那些情感、思想和文化价值,恰恰是后者所缺乏的:简单幼稚拒绝思考的积习和「小清新」萌化的浅薄文化欣赏习惯,让台湾电影从本来的高点向下无可抑制的下坠。
特别致命的是,岛内党派和族群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挑动了对某种传统的拒绝和切割。而正是这种深深影响侯孝贤的传统对树立电影的核心创作价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海上花》
在硬性剥离思维传统后所留下的空白被博出位的娱乐至死、泪腺偾张的无度煽情以及廉价肤浅的情感表达所取代,它让台湾电影的创作者们在思想意识上停步不前,在价值观表达上浮躁而流于表面。
如果说侯孝贤通过《刺客聂隐娘》带来的金棕榈光环宣示他所坚持的一贯电影价值观,那么与之态度相背离的时下台湾主流电影则很可能是在走向一条不能回头的没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