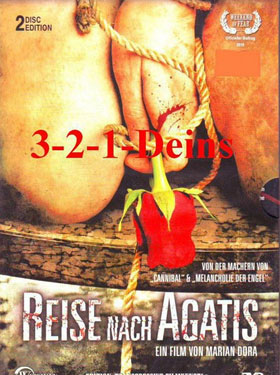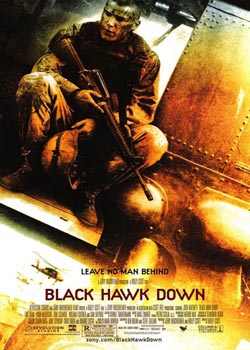因为有他这样的导演,让我们对国产片还保留期待
2015-11-02
毒Sir
毒舌电影
毒舌电影
这段时间,因为《山河故人》,贾樟柯再次频频见于各大媒体。
“文艺导演”再次受到了关注。

《山河故人》两天票房已超贾樟柯过去电影国内票房总和。
Sir前段时间也有机会采访这么一位,所以,今天想跟你们说说他。
除去还没上映的新片,因“朝阳区群众”而被无限期押后的上一部,他的作品在内地银幕只公映过两部。
一部豆瓣评分7.5,另一部8.3——甚至被部分人称为2011年最好国产片。

但前者票房可忽略不计,后者也不过六百多万。
说到这,也许有部分毒友已经猜出。
是,Sir想说的是张猛。
这个因为还有一个“电影梦还没实现”,从本山传媒副总岗位离职,却至今未得到市场承认的“小众导演”。

张猛出生于东北辽宁一个文艺家庭。
父亲张惠中是知名喜剧导演,导过小品包括但不限于《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卖拐》。

还有赵本山影视处女作《男妇女主任》。

母亲陈佩云是职业演员,曾在1984年跟赵本山合作《摔三弦》——这也是赵本山成名作。

或许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张猛高三毕业,就想考北京电影学院,
但当年北影没有在辽宁招生,他只能去父亲母校中央戏剧学院,学舞台美术。
1999年毕业,他被分配到辽宁电视台做舞台美术总监,但他一点都不喜欢。
就是千篇一律,有一个栏目就去倒腾个景,不该你管的,永远都不能去涉及,没劲,没创造性。
他还是想拍电影,干了一年,辞职,去北京电影学院读那种“花钱就能上”的导演进修班。
北京一年半,他遇到一部“挺牛”的国产片——贾樟柯的《小武》。

当时他和宁浩、朱传明等都是地下电影小组成员。
都被《小武》震了——一下就把我们这些年轻导演带回到那个你特别熟悉的环境。

这种记录时代的粗糙与生猛,在推崇宏大叙事的中国银幕,很罕见。
但牛归牛,新千年左右是中国电影寒冬——连续几年票房总量不到10亿,没人会给新人埋单。
为了练手,张猛只能做枪手,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廉价剧本。
在泥潭般的生活中,2002年,他还是拍了一个纪录片《耳朵大有福》,讲一个工人退休第一天的生活。
这时候,离他拍出第一部电影还有5年。

2004年,他回到家乡沈阳,因为在听父亲和赵本山商量春晚小品时插了一嘴,赵本山一听很对味,按他的建议,捣鼓出《功夫》。

之后张猛子承父业,写小品,二人转,职业曾一度是本山传媒副总。
小品与电影不一样,台下观众的反应是即时的。
当时每写一稿,演员都会带着剧本见观众,所以,张猛很清楚,观众会在哪个地方笑。
他开始摸索,研究用什么样的语言能打动观众。
这些小品在市场反映上掌声颇丰,但张猛始终觉得,“写小品是在打工,电影才是真正的自己的东西”。
2006年,在看到曾经同为地下电影小组成员的宁浩拍出《疯狂的石头》后,张猛感到不能再这么耗着了。

他决定辞职。
与绝大多数新导演一样,海外影展是张猛的第一站。
凭借根据纪录片《耳朵大有福》丰满出的剧本,张猛在釜山电影节获优秀剧本奖,拿到85万人民币。
再搭上自己的积蓄和朋友那借的80万,处女作终于开机。
第一次当导演的张猛并不敢对票房有过多的期待,也没考虑做成类型片,完全从个人出发。
在当时的他看来 :
能拍自己想拍的,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一部“任性”的电影——《耳朵大有福》。

故事的主人公,是东北老工业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策改革下,面临下岗,劝退命运的工人阶级。
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一文中曾记载:
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有超过两千万的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
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几万元钱就被扔到了马路上。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甚至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

这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抛弃的群体——当然,他们不是第一次被发现。
王兵《铁西区》曾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铁西区》极度真实地记录下沈阳一家大型工厂的工人们,在工厂倒闭后,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终日喝酒,打架,对着电视机看歌舞晚会或者毛片。

同年,贾樟柯《24城记》也表现了下岗工人做零工,卖体力维持生计的心酸。


无疑,《耳朵大有福》的王抗美也是这样挣扎求生的小人物。
当了一辈子铁路底层工人,年纪一到,拿着微薄的退休金,离开工厂。

妻子重病住院,家里情况不好,一下子收入锐减的王抗美只能找活干。

他到街上蹬车,因为气管炎,蹬不了几下就上不来气。

去网络公司应聘被骗进传销组织。

这是一个社会变革中的弃婴,王抗美(就连名字都可被当作笑柄)有足够理由哭丧着脸过日子。
但张猛不想卖苦。
在他看来,东北人的处事方式天生乐观,即便苦,也能苦中作乐。
所以,事事不顺心的王抗美路过一个电脑算命的摊子,会忍不住算一卦。
做个形象设计。

虽然被生活折腾得疲惫不堪,还是相信——

愁也一天乐也一天,不乐多冤哪。
因为算命姑娘的一句“耳朵大有福”,甚至掏出大钱(十块)当小费。
这就是典型的东北人。
我在家再难受,我出门也要穿的立立整整的,我也要有个面儿,这就是一个极其阳光的生活状态,我不会把阴霾的一面给你,越苦我越不能说苦。
幽默,成为他们与现实斡旋的最后武器。
这种滑稽的伤感在张猛第二部作品——《钢的琴》中更进一步。
《钢的琴》的灵感来自张猛许多年前,在铁岭给姑姑设计服装店面时,看到的一架破钢琴。
他爸告诉他,那是70年代一帮文艺工作者自己画图纸,整材料做出来的。

后来他又在钢材市场里遇见一群手艺很好,但因为下岗,混吃度日的工人。
两者相结合,就成了《钢的琴》的主角们。
他们从一家倒闭的工厂刚刚出来,除了掌握一门过时的手艺,两手空空。
为了谋生,他们成了小偷,保安,赌徒,杀猪匠——

曾经是“最光荣的工人老大哥”,在不适应中灰头土脸地生活着,到处给人点头哈腰。

但在巨山般的困境面前,他们仍打肿脸充胖子。


喜欢见缝插针地自娱自乐:

连扮演陈桂林的王千源说起这个人物来都憋不住笑:
西方的绅士都穿西装,打领带,他就穿一个特不合身,特别破的西装,戴个破围脖,手上还拿一杯就5毛钱的茉莉花茶,整的还挺像在欣赏歌剧似得。

仔细看,西装下还能看见露马脚的绿毛裤
这就是张猛特别的地方。
在他的逻辑中,泪点与笑点就像硬币的两面。即便现实对老百姓百般嘲弄,但他们总有办法用幽默跨过去。
他们不会像英雄般觉醒,也绝不低头认输,比起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心灵鸡汤,或沉溺于苦闷的常规语境中,这种从困境中磨砺出来的自我开解,无疑更质朴,也更具生活质感。
就像张猛非常欣赏的电影《顽主》。
《顽主》里:他们会笑,但是以悲的方式笑;他们保持清醒,但是以醉的方式。

所以,张猛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他在拍片时遇到的困难。
甚至,物质的艰辛都不算什么。
拍《钢的琴》,剧组的人因为挡了工人回家的路,挨了两次打。工人不理解他们,“也不愿意你去拍,自贱的感觉,就会觉得你拍我们干嘛,我们有什么好拍的。”
张猛无奈,自我安慰,“他们心里的那种失落,可能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拍《胜利》,电影拿下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因为黄海波事件,电影从去年就拿到龙标,但到现在还是上不了。
张猛也只能自嘲,下部片要避开“朝阳区群众”。

他更爱谈自己电影有感而发的细节。
比如年轻时是愤青,“哥们谁说有什么事儿要出去打架,立马就说,走!”——就像他喜欢的老港片里“盲目的英雄主义”。
这种情结,就变成《钢的琴》中,大门洞开,陈桂林和他们的伙伴,集体呼啸而出的场面。

当然,张猛并不是一个一味死扛的人,就像贾樟柯,王小帅们一样,他也愿意尽最大努力找到自己的观众。
他曾经说过,自己迟早要拍商业电影。

今年12月4号上映的《一切都好》是张猛的第四部电影,是他告别”东北三部曲”首作,也是他至今投资最大的一部作品。
在此之前,张猛签约了大河影业:
因为后者保证了他的创作自由的同时,也分担了商业压力:
除了对我个人的表达自由很支持;从整个市场来讲,不管钱多钱少,它也能给你一个保障,让你在融资容易得多。
从故事与牌面看来,《一切都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贺岁片——合家欢喜剧,同时囊括了张国立,姚晨等一线明星。

档期选择也很聪明。
就是在一个大家都想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一些共鸣,我觉得会跟大家往家赶的情绪有所呼应。
今年以来,持续升温的中国电影市场催生了好几部10亿大片——当中大部分都是喜剧,《煎饼侠》,《港囧》,《夏洛特的烦恼》。
张猛《一切都好》能不能借势而上?
目前电影曝光物料不多,按照《毒舌》不见兔子不撒鹰的风格,Sir不轻易推荐。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闹天宫》制片人王海峰先生曾公开表示对张猛的欣赏:
我一直想找他合作,但他不理我啊。
王海峰说:
周润发当时看完《钢的琴》,喜欢的不得了,一直要我约张猛谈合作。可他竟然回答我说,没空,因为他有剧本还要写。这虽然让我有些没面子,但是他对故事的追求,对剧本的打磨,让我倍加佩服。
不知怎么的,Sir听到这句话时,莫名想到了《耳朵大有福》一个画面。
范伟,心无旁骛,一板一眼地干他最爱也最擅长的事——修理自行车。

正是这份认真,让我们对这个下岗工人,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敬重。
这是手艺人的尊严。
也是Sir个人期待《一切都好》的最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