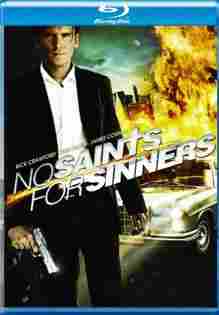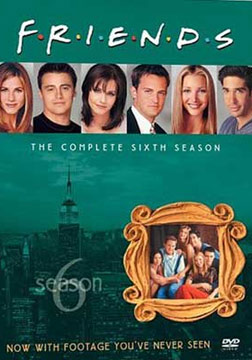“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曾经十六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说我得了一种怪毛病,医学上叫做演员狂想症。我喜欢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身份,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由于我喜欢的是真实可信的演出,因此在我的演出中的演员,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装腔作势的演戏。只可惜,我两手空空,没法付给他们报酬,我就向财政部申请赞助,但是由于我没有政治靠山,所以他们不给我钱,我就在……”
这是陈建斌在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一段台词。演话剧时是1998年,陈建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毕业,28岁,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大龄毕业生。多年来,他在影视表演的道路上走得坚实而稳重,像他的嗓音,浑厚有力。不过,陈建斌做导演却是有点出人意料,至少是相当低调。去年,在金马奖颁奖前夕,《一个勺子》曾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媒体放映,由于此前这部影片的消息少之又少,不少媒体都因为工作繁忙(实则是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未能到场,谁知,这部电影竟然在金马奖上问鼎了三项大奖,堪比今年大获全胜的《刺客聂隐娘》。这让不少没有看片的媒体记者追悔不已。
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勺子》在精神气质上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有些近似,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疯子,都在与所谓正常人的交锋中,改变了他们的处事方式与价值标准,两部作品都在探讨存在的意义,以及世俗陈规的相对性。《一个勺子》质朴又真实,基调轻松,荒诞不经,却又能够让人触摸到生活的质感。谈及影片本身,陈建斌援引电影《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台词,形容《一个勺子》的拍摄过程:“是痛苦,也是快乐!”而据同窗室友李亚鹏说,上大学时,陈建斌在自己宿舍的柜子上刻着四个大字“享受痛苦”。
在与陈建斌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文艺风情,他说刚刚看过瓦伊达的《灰烬与钻石》,并且对这部1958年的电影称赞有加。他的老婆蒋勤勤则说他就是“一个勺子”,这电影就是拍的他自己。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的善良、困惑、彷徨、呐喊以及无助,或许也正是这位文艺中年的自我写照。

《一个勺子》剧照:拉条子给“捡”来的勺子洗澡。对于一个“失去”儿子的中年男人,这个勺子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替代。
电影的荒诞,是因为生活本身的荒诞
猫眼电影: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感觉和你早期演的孟京辉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精神气质上有些相似,你有这个感受吗?
陈建斌:(笑)还真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也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真的有吗?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有,但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过这个电影。
猫眼电影:那部话剧是1998年,你从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在那个戏里头,你的角色是个疯子,到了《一个勺子》里,这部电影的核心是一个傻子(勺子)。这两个人物有一种相似性。
陈建斌: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为什么我对这个都这么感兴趣啊?(笑)
猫眼电影: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对正常人的交锋过程中,影响到了正常人所谓的观念,导致最后不知道谁是疯子、谁是傻子。
陈建斌:对对对,《无政府》里边也是,最后警察都疯了。
猫眼电影:的确这两部作品有相似性,包括那些荒诞的处理手法,在《一个勺子》里头也有很多荒诞的笔调。你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整体的基调设定是什么样的?这种故事中的荒诞性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吗?
陈建斌:还真不是。一开始想写一个特别真实的电影,还是要从写实的角度出发。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最后是这个情节使然,故事发生到后来的时候,情节就变得很荒诞。但是说到底,这些荒诞都比不过现实的荒诞。我觉得有些新闻,看上去比我的电影荒诞多了,真的是超现实的,都不可想象的。但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家看的时候也就接受了,因为是真实的。假如有些新闻变成电影之后,你都不会相信,你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两者的区别才是真正的荒诞,就是现实和艺术创造的荒诞。
猫眼电影:你之前跟蔡尚君导演合作的《人山人海》也是这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拍成电影之后可能大家也会怀疑,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千里追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真实的。
陈建斌:对,他只是把五个人改成了一个人,原本是五兄弟。也是很傻嘛!你有正常的生活,但你又可以把你正常的生活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来不该你做的,应该有专门的人去做的,但是你去做了,那就很傻。

《一个勺子》剧照:陈建斌饰演的西北牧羊人,憨厚淳朴,内心中又充满良善。可是到头来,却成为别人眼中的傻子。
《一个勺子》=陈建斌自传
猫眼电影:无论中外,对于很多导演来说,他们在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和自传经历。那么在《一个勺子》中,有没有跟你的成长经历相通的部分?
陈建斌:从你这个角度和观点出发,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当作我的自传了。一方面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农村生活,我小时候七岁之前都是在农村生活,我对那段生活“耿耿于怀”,到今天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另一方面对人物的状态,傻不傻的问题,如何摆脱你身上的傻,以及摆脱之后如何怅然若失,成为一个更傻的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我的生活啊!我其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个人。比如说在以前的创作之中,他们经常说“逾矩”啦,作为一个演员,又干导演、又干灯光、又干美术,什么都想参与,真的是很傻,别人觉得傻,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自己的傻。过了好多年,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当时那么傻?我干了那么多活,还没落下好,人家还觉得我怎么着了。这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傻了吧!下面就是要摆脱这个,“我不说了!朋友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想再做那个傻子了!”但是摆脱这个“傻子”谈何容易啊,因为他是你自己,你总是在跟自己较量。好不容易摆脱了,那就成了一个中年大叔,一个微笑着的中年大叔,别人说什么都是“好好好,可以!”然后呢,突然发现,我不再是我了,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我觉得这就变成了一个更傻更傻的人。
我这是举例子,不一定准确。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拓展到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二十多岁出道,来到社会上,带着青涩、带着锐气,过关斩将,然后跟人拼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也受到了伤害。快三十多岁了,才觉得这不行啊,这有问题,我是做人有问题,还是怎么着?我必须得升级我自己,怎么升级自己呢?就是先认识到从前那个我不行,人家都说我是个傻逼,我得成为一个精逼,我得聪明,就要摆脱自己。摆脱谈何容易啊?我认为摆脱至少要用了十年,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努力克服,努力抗争,然后到了四十岁左右,有了家庭,挣了一点小钱,有一天突然照镜子,“我操!镜子里边这个人是谁呀!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曾经想成为的那个我。这个人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人。”什么叫中年危机啊?概莫能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经过跟别人拼杀,跟自己拼杀,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你小时候最讨厌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个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丧失了自我,你能说他是个聪明人吗?他是一个最傻最傻的人。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是这样了。一般人的心路历程,都是如此。难道不是吗?
猫眼电影:《一个勺子》看完之后,还有有意思的一点是人物关系的设置,勺子、拉条子、大头哥,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关系,两两搭配,组成了两对关系。这是最开始就设计好的主线吧?
陈建斌:小说就是这样。为什么我看中这个小说,就是小说里用特别简单的几个人物,就把简单的食物链形成了,从最底层的农民到他们镇子上的首富,他就代表这个镇子的食物链的顶端,开着一辆“猛禽”。我觉得最好的剧本就是这样,用最少的人物关系,就能辐射出整个生活。不要看到它的背景是农村,如果把这个背景都抛开,可以是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我这个电影结尾讲的就是,你觉得别人很傻,你觉得这个勺子很傻,那大头哥还觉得你傻呢!比大头哥更牛逼的人觉得大头哥也傻!就是这样。

《一个勺子》剧照:这部电影中的勺子由金世佳扮演,他抛弃帅气的外型,反而打扮得像个邋遢的“耶稣”。
勺子,就是耶稣?
猫眼电影:其中有一场戏,拉条子把勺子绑在一个柱子上,用了一种耶稣式的、宗教式的绑法。后来一想这部电影中还有羔羊、牧羊人等等这些符号,这是巧合吗?还是说你有意识地往这部电影中植入了一些宗教色彩?
陈建斌:这个小说里写的就是牧羊人,不是我编的。在小说的基础之上,生发出来的,就是勺子这个形象,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欲无求,他不为自己,只为别人,这样的人如果搁在生活里,你一定觉得他是个傻瓜。假如说耶稣,现在来到你的生活里,你一定觉得他脑子有病啊!但是你又怎么能知道你碰到的那个傻子,他又不是耶稣呢?当时耶稣在他的时代里,又何尝不是一个别人看起来的傻子呢?他为什么会被被人绑到十字架上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被人觉得他有问题啊?对不对?当时的执政者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至于牧羊人那个身份呢,他儿子不在,他有一群羊也有小羊,这些都是原小说里就有的。后来出现了一个傻子,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洗干净了跟他儿子还很像,这些都是小说里的。只是引申过来,缺失的儿子用羔羊来代替,这个是电影里新加的,然后这个傻子出现了就成了他儿子的替代品,你看后面有一场戏是傻子被人接走的时候,拉条子的老婆已经在收拾他儿子的房间,就是想要让傻子从羊圈里搬出来,住到他儿子的房间。但就是那天晚上,傻子被带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羔羊和傻子,都是牧羊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但是当一切被搞得稀里糊涂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宰杀了这只羔羊。为什么呢?宰杀羔羊之后跟他能碰到的村里的最聪明的人,也就是三哥,要请教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困扰他了。为此他可以杀掉他心中最软弱的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人为什么发出疑问呢?发出疑问的原因就是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怀疑,为什么要问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去请教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如果问题这么容易就能回答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就不用拍了。我们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提出问题,没有答案。但我们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是像拉条子一样做,被人看成傻瓜呢?还是你就像大头哥说的,断然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你会如何选择呢?还是说你做了以后,你会觉得自己错了,然后你会否定自己,干掉自己。
猫眼电影:其实这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模型。
陈建斌:是,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斗争。我应该如何成为我自己?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你由着自己成长是不行的,你是要遭受到许多的磨难和打击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那就要改变自我,就要把你心中的羔羊给杀掉,否定自己,改变自己,适应大家,你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
猫眼电影:关于人的疑问,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你现在还会像拉条子一样,存在这些疑问吗?
陈建斌:当然。为什么喜欢这个小说呢?就是这个小说把这些可能性都实现了,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一边看,文字就转化成画面,一部电影的雏形就出现了。这就是我想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我所有的疑问都装进去。
猫眼电影:而且还是可大可小,小了就是生活里的一个小事,就是五万块钱的事儿,大了就是一个人生的终极命题。
陈建斌:对对对,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就是很小的一个事,就是一个勺子怎么怎么地,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事。这部电影就像一面镜子,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对生活的认识。

《一个勺子》力求还原生活的真相,为此,陈建斌也试图效仿张艺谋采用偷拍的形式,谁知GoPro不靠谱,最终没能实现。
偷拍,是最大的难题
猫眼电影:这是你第一次做导演,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很难过关的地方?
陈建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偷拍”。因为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很多遍《秋菊打官司》。《秋菊》里边很多戏都是偷拍的,是提前把机位埋好,而且不是一台机器,是几台机器埋好,演员走在人群里。所以那个电影才是那么的生活,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些是表演哪些是真实)。我们也想这么拍,而且我想升级,你想《秋菊》那都是十几年前的电影了,我们现在的设备也都升级了,我应该拍得比他更鲜活。
我们就准备用GoPro拍,这个摄影机很小,就装在摄影师的帽子上,根本看不出来是在摄影。这样就可以深入人群,“偷拍”到人群的中景、近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想法当时简直把我都震翻了,太牛逼了!然后做实验,找了一个菜市场,摄影机从屋里出来一直到屋外,再到屋里,实验也都没问题,当时觉得太牛逼了,这简直是划时代的!再然后就去甘肃拍摄,有一天我们就拍了一早晨,因为担心素材,中午就拿回去检查,一检查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做实验的时候是在北京,也是冬天,加上雾霾等等原因,光照度不够,所以屋里屋外没有特别大的反差,就可以。但是甘肃一出门就是蓝天白云,所以从屋里黑的地方一出来,光照强度的对比就特别强烈,GoPro的宽容度就不够,就没法用,那一早上拍的东西都不能用,而且证明了GoPro不靠谱啊!没办法,又回到了原来的传统的拍法,就是在车里藏好然后开始拍。

为了支持爱人的事业,蒋勤勤也“自毁形象”,扮演了一个土掉渣的村妇。在这部电影中,她的表演同样非常精彩。
猫眼电影:为了拍这部电影,你也找了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
陈建斌:对,(王)学兵这是我同学,(蒋)勤勤是我老婆,“卖瓜子的”是我同学,“李大头的老婆”是我同学,“李老三”是我同学,“村长”还有“警察”都是我的朋友,是我从新疆调过来的,他们都是非职业的。复印店那个小老板,就是那一家复印店老板的儿子,一直到我那天早上去拍戏,演员都没定下来,坐在那儿正发愁呢,突然我看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在晃悠,我说他是谁?他们说这是这家店老板的儿子,我说就让他来演!演得非常好,因为他不用演,本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店。这些演员都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你在里面分不出派别,也分不出谁是职业的,谁是非职业的。

《一个勺子》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出手不凡,这也源自于陈建斌多年的积累和沉淀。 他追求写实的电影理念,也极具作者风范。
我不要美化生活,也不丑化生活
猫眼电影:以前采访贾樟柯导演的时候,他也说自己的经历,那时候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看完之后就被大银幕上的生命力给震撼到了。在你的经历中,有没有哪些电影让你为电影的魅力所折服?
陈建斌:有的有的。包括像老贾说的这个《黄土地》,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热别震撼,电影结尾的时候,人群往那边走,但是憨憨一个人逆流而上。那时候我才十几岁,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那里面讲的是什么,但是那个画面给你的震撼,你会觉得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会停在你的心里,然你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有魅力的画面?等我真正的十七八岁,我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红高粱》的时候,到了“颠轿子”那一场戏,我就直接在观众席上站起来了,就是激动的,完全征服了你。它的那种昂扬的情绪,还有姜文在里面的表演,竟然还有这样的表演!另外就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在新疆。德帕迪约也是属于那样的演员,他的故事讲的是后台的事儿,排话剧的事儿。我深刻地记得电影最后的几句对白,德帕迪约看着德娜芙说:“你真美,看着你是一种痛苦。” 德娜芙就说:“可你昨天还说是一种欢乐。”德帕迪约说:“是痛苦,也是欢乐。”这是电影的结尾。我操!我真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是痛苦也是欢乐。包括我做这个电影也是,经历了很多欢乐的时刻,也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刻,加在一起就是“您真美!”
猫眼电影:最近这些年,中国电影在农村题材、西北题材的领域中,很少,粗砺的、生命力旺盛的电影,特别少。
陈建斌:我拍之前,就想看一下咱们之前拍的农村题材的电影,有好的可以借鉴一下,我翻来翻去,之前最好的还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猫眼电影:对,《秋菊打官司》所提供的影像风格,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特质。《一个勺子》的影像风格也是你跟赵小丁商量过的结果吗?
陈建斌:是我们选择的,想要一种粗砺的、直接的、生猛的,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像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拿一个手机,动来动去,唰唰唰,这是我想要的。我最开始跟赵老师就说,我们这个片子“不带装修”,我真是特别反感咱们的电影里有太多的“装修”,我很讨厌,很虚假。我不要美化生活,我也不要丑化生活,我先正视生活,生活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里面的人、里面的景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首先做到真实,然后再讲自己的东西。
电影叫什么?电影叫真实的艺术,无论什么电影,首先得要真实。你看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拍的也很真实,并不是因为科幻了就胡拍,弄得特假,不是,反而越科幻越真实。影像上必须真实,表演也必须真实,这是一个前提,在真实的基础上,你去讲故事,这个故事讲成什么样都可以。
(采访、文/亚伯;摄影/小强;编辑/该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