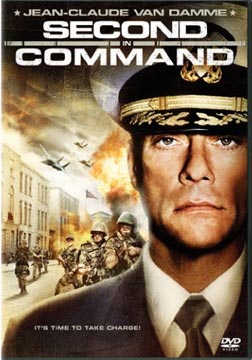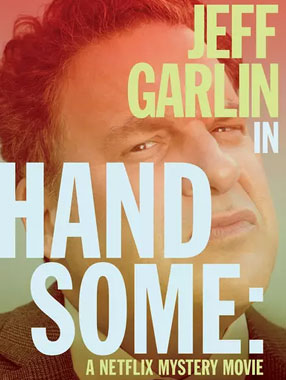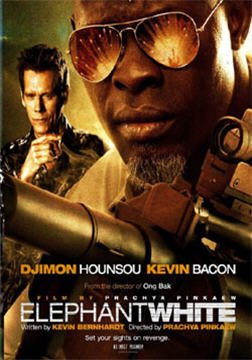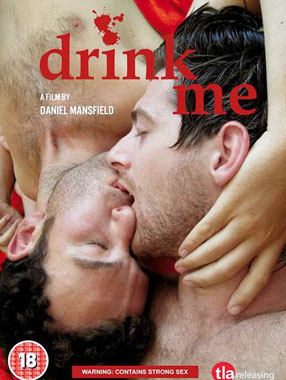舒淇的最迷人之处,在于她有一张几乎能代表世间女人对男人最情深意重的脸庞。往事经年,无须提及——
我们要说的是,这是看起来很美的又一年时光。从去年底的《一步之遥》,今年中的《落跑吧,爱情》、《聂隐娘》、《剩者为王》,直到年底盛大上映的“鬼吹灯”之《寻龙诀》,这一整年,舒淇的大银幕作品今年就没有间断过。但外人也许不那么知道的是,如此高产绝非仅因舒淇众所周知的不俗演技,这其中的很多电影,对她而言,接下完全是因为“情意”二字。
“《聂隐娘》我答应侯导的时候,话说是7年前……《剩者为王》是华涛亲自拿给我看的本子,哪里知道他最后做了监制……《落跑吧,爱情》是小齐第一次当导演……都是那么久的交情,就不要讲年纪了!”
有时看到她,就像比照自己: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弱水三千,当你足够强大,才可以只取你爱的那一瓢,强大并不意味着包揽与得到一切,而是甘心情愿地对值得的人和事承诺但未必明说的那三个字——那三个在爱情片《剩者为王》的结尾里,舒淇没有对彭于晏顺理成章说出口的,同样在奇幻片《寻龙诀》里借Shirley杨之手对陈坤饰演的胡八一表明的:
我愿意。

舒淇的采访约了很久,久到我都已经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等待下一场采访那样,貌似漫长无尽的等待。
这个冬季京城的黄昏,尤其难熬。窗外,目力所及,就像《聂隐娘》里静到几乎不动的长镜头,看雪漫绿地、星星点点,看雾霭茫茫、宛若前程,看天慢慢地暗下来,连背后的猫都在不耐地叫唤。
在那个也许境遇相同的三十岁的黄昏里,舒淇在做什么呢?“我忘了,应该都在拍戏吧,反正我入行到现在好像都在拍戏吧。”年龄这回事大约就是这样,让一些原本觉得很重要、重要到难忘的一些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明明近在咫尺,但她的声音好像悠远得是从貌似很远的地方飘过来—远观或是近瞻,常年长发如海藻般微卷披散下来的她无论身着哪一件华服,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普通时尚杂志红唇大眼的那套把戏根本不适合她。她利落又天真,眼神有可以扮演杀手的狠,声音里却有挥之不去的娇嗔,饱食人间烟火而不俗是舒淇特有的美感——眼下,她的美像美人鱼那般从海面上懒洋洋地、冉冉地升腾起来,她周身的气场就像是充满了金色的、易碎的香槟泡沫—让人轻易觉得,咄咄逼人地问她任何问题,都是不适合的。
其实本就如此:大多有关人生的问题,都应该问自己,而不是问他人。但无论如何,舒淇都是我今年采写的最后一篇女明星特稿,必须承认,当年过三十,你也很难再对他人持有专注的兴趣,人们喜爱一部电影、一帧画面、一个明星—无非因为,她像某一部分曾经或当下的自己,或者理想中自己未来的样子。
我向来觉得,舒淇的最迷人之处,在于她有一张几乎能代表世间女人对男人最情深意重的脸庞—女人喜欢她,因为看到曾经对男人、对爱情深情的自己;男人喜欢她,却是因为她不曾因为爱情深刻地改变自己;女人爱她,因为她复杂—那不是人人敢和可企及的历经世事;男人爱她,却是因为她简单—复杂后还能够简单直接,如同爱情最初袭来的样子。
而在电影之外的舒淇,不止一人告诉过我,她是慢热、寡言的——对人的接受有漫长的过程,同时本能地拒绝一切,“我不要”是她平日的口头禅之一,而她在这次采访里也亲口对我承认:“如果真的做自己,很多时候我就不想讲话。”这让面对她的时候,在很多短暂沉默的间隙,那些她主演的经典爱情电影的镜头有了更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脑海的理由—我得承认,这个黄昏,我想到的最多的还是《玻璃之城》里的那个黄昏。有些电影换二两个人演绎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比如 《心动》里的梁咏琪和金城武,《大话西游》里的朱茵和周星驰,而在《玻璃之城》里,永恒的是学生时代后重逢的舞会上,隔着烛光和歌声,舒淇回眸注视黎明,镜头定格在她娇俏的微微一笑里,但你无法忽略的是,她的眼中有无限唯有她才自知、绝不会向外人用言语道出的深情。

往事经年,无须提及。无可否认的是,这是看起来很美的又一年时光——从去年底的《一步之遥》,今年中的《落跑吧,爱情》、《聂隐娘》、《剩者为王》,直到年底盛大上映的“鬼吹灯”之《寻龙诀》—这一整年,舒淇的大银幕作品就没有间断过。
但外人也许不那么知道的是,如此高产绝非仅因舒淇众所周知的不俗演技,这其中的很多电影,对她而言,接下完全是因为“情意”二字。“《聂隐娘》我答应侯导的时候,话说是7年前……《剩者为王》是华涛亲自拿给我看的本子,哪里知道他最后做了监制……《落跑吧,爱情》是小齐第一次当导演……都是那么久的交情,就不要讲年纪了!”舒淇用她特有的说话方式阐述这一切,“所以其实,对啊,就是这样……”不多久,舒淇身边的人叫她:小姐,该去工作了。“对不起。”她盈盈起身—女明星的累,是一种无处遁形,角色被揣度,必须要言语,肉身飞来飞去——有时看到她们,就像比照自己: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弱水三千,当你足够强大,才可以只取你爱的那一瓢,强大并不意味着包揽与得到一切,而是甘心情愿地对值得的人和事承诺诺但未必明说那三个字—那三个在爱情片《剩者为王》的结尾里,舒淇没有对彭于晏顺理成章说出口的,同样在奇幻片《寻龙诀》里借Shirley杨之手对陈坤饰演的胡八一表明的:我愿意。
事实上,人世间最难偿还的,就是这样的情意—最能生发出奇迹的,也是真正的情意。我想起,这次采访最终能够得以达成,和那个春天我孤身一人拖着箱子从广州去往香港不无关系,而我也终于理解了彼时她说的,“她总是飞来飞去,太让人心疼了。”当我把关于“情意”的前半句配上一张不太多见的《玻璃之城》剧照发在了那天的朋友圈里后,曾经盛赞舒淇在《剩者为王》里自己给自己披上婚纱那段长独白戏份、深觉她正在“演戏巅峰状态”的滕华涛,第一个留言问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其实——这真的——一言难尽啊。
就像我们对舒淇“深情”倾注的几多情意,她在电影里“自知”倾注的几多自己。

深 情
这世间适合演侠女的女子并不多见——要主演大银幕上的侠女而不露怯,必须本质里有足够分量的义气与侠骨。
舒淇这一年一演就是两个——Shirley杨和聂隐娘,都是看似冷酷,实则深情但不要对方领情的人物。
“相似,也不一样。聂隐娘她是属于比较内敛的,她算是一个悲剧人物吧,悲剧近年来我都不是很想接,但因为我那时候答应侯导,话说是7年前,结果他拖了那么久才拍,到他正式开拍的时候就隔了5年吧,然后拍就拍了2年。”舒淇自己这样解释说,“而Shirley杨是比较外放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女生。”
对舒淇这样颇具天赋的女演员而言,难的大约不是诠释悲剧或是奇幻、内敛或是外放,而是同一时期两个角色的状态切换。去年冬天在北京拍摄《寻龙诀》期间,舒淇曾被侯孝贤召唤回去补拍《聂隐娘》一整个礼拜,“这边是商业片,所有东西都往外面放;那边是艺术片,所有东西又都往里头收,现在一想起来,就是很累,很烦,这种感受是没办法讲清楚的……”她并不太愿意多回忆那时的事情。譬如,作为刺客的聂隐娘被威亚吊至房顶或树端,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一场每天凌晨4点从4米高的树上往下跳的戏,畏高的舒淇一连跳了四天才过,因为每天只有那个时刻,可以拍到太阳初升中的人影勾勒—因为信任,侯导不说,她便不问。“这样说来,幸好还有Shirley杨。”舒淇如今回想起来说,“她是一个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会为自己发声,最后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她还会反过来去安慰胡八一,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她是比较像男人,比较硬朗一点的女生。”
其实,即便脱离《寻龙诀》的摸金三人组身份,Shirley杨都是一个光芒四射的现代派女性角色。我看完电影的观感是:这真是一个敢于追男人的女人——在纽约的开场,身着红色皮衣的她身手矫健地帅气驾车、救出三人组里的另两个男人;在内蒙古草原上,她爱的男人骑马,她二话不说翻身骑上摩托追他;在地下世界里,身着军绿色背心、麻花辫甩在脑后的她,活脱脱就是中国版的劳拉——但我不得不说,在打戏之外,被舒淇彻底演活、更引人入胜的,是她与胡八一之间看似火爆、实则情深的感情线戏份:她经常不看着他,说出的话却一句比一句狠:“我妈告诉我,和一个男人上了床,如果他不联系你,不要主动联系他”、“你们男人都这么不负责任是吧”;面对一个惦记初恋、难以展开新恋情的男人,她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俩的事情有什么好捋的, 你的态度说明了一切”、“我允许你后悔”;她一次次离去,却又一次次转身回来:“胡八一,你这个自私自利自作聪明的自大狂,你们男人加在一起就是trouble!”
“对Shirley来说,她爱这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好像还有一些秘密她不了解,这个秘密就藏在地下,到底他内心里面的隐痛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回忆阻碍他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去爱他应该爱的人。”《寻龙诀》的导演乌尔善对我解释Shirley杨这个人物时说,“我觉得对女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探险的过程吧——进入她爱的这个男人的内心。”

你想不出除舒淇外还有无第二个人选,能把这些骂人的话说得如此具有个人特色而让男人不觉得烦闷,就像结尾Shirley杨把胡八一搂在怀里说“大不了一起死在这儿”时,他对她说的台词:“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最喜欢你骂我的样子!”;更不用提地下世界里,当王凯旋对胡八一喊“我王凯旋爱一个女人,会记她一辈子!”时,镜头却微妙地转向Shirley杨,她给了一个完全是舒淇招牌式的欲说还休的眼神。
乌尔善对这场戏印象深刻。“ 舒淇她是—直觉非常准的一个演员,她虽然不怎么说技巧,不怎么说她的设想,但是她给出来的反应往往是特别准确的。”他评价说。在那段戏里,王凯旋对胡八一喊完后是对Shirley喊说“你当然不懂,我们这叫革命情义,我随时可以为小丁(注:王凯旋和胡八一共同的初恋丁思甜,为救王胡二人而牺牲,Angelababy饰)去死”,原剧本给舒淇设置的台词反应是“幼稚”。“我说你说一遍这个台词,她说得很低,后来她就说,导演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说话,说话我觉得不太对。”乌尔善回忆说,“我当时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我说你就这样两种都给我演一遍吧。但最终剪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不能说话—因为这个时候王凯旋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想舒淇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理解,无论对方处在什么样的情绪里说你不懂我,她都不应该再去跟他去做斗嘴这种事情——最后我用的表演是,她没说话,把眼神低了一下——这个表演就特别准。”
舒淇自己和导演一样印象深刻的则是另一场在水下的棺材里挣扎的戏——在胡八一对Shirley杨说完“我最喜欢你骂我的样子”,舍己把她救入单人棺材后。“那场戏真的很难拍,要躺在棺材里头,手跟脚都不可以出画面,然后还要发泄那种真实离别的情绪……机器其实就在你前面嘛,又需要去控制力度,要不然就把摄影机给砸碎了。”舒淇说,“那场其实真的特别难,因为你要把情绪点都放出来,可是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所以那场戏我觉得属于难演的。”
“那场戏大概拍了几次啊?”我追问。
“以我的功力,应该不会超过三次吧—应该一两次吧我记得。”舒淇笑言,“对,我忘了。”
这就是舒淇式的可爱—她甚至都忘了,那一场情绪发泄,除了“胡八一,你这个王八蛋,你让我出去!”,后面的台词都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她说这段应该再长一些,她后面加了很多她自己的台词发挥,譬如谁会喜欢你这样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说挺好的,这应该就是你,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本能的反应。”乌尔善告诉我。
“自大狂——我说挺好的,这应该就是你,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本能的反应。”乌尔善告诉我。
“她很坚强。”乌尔善沉吟了一下,“她不愿意说那些博取同情的话。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

自 知
因为自身个性中敢爱敢恨的特质,舒淇的演绎让Shirley杨这样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非常让人信服——朝夕相处的剧组中人,都难免将她们重叠起来。“舒淇台下什么样,上了台还是什么样,演的都是她自己。”有人私下这样对我说。
非演戏科班出身的舒淇,难免总会让人有这样本人和戏中角色重叠到浑然天成的错觉。“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她之前演的一些角色都是浪漫爱情故事,总演那些纯情的、为爱所困的女孩。但其实当时找舒淇的原因就是,我是觉得舒淇本人应该是Shirley杨这种。”乌尔善说,“在《寻龙诀》这个电影里面,经历了一个反转,开始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假小子,非常强势、泼辣、利落,但她其实真正内心是一个需要爱的小女人—我觉得舒淇自己有真实的两个极,因为她之前很多角色没有把她的能量释放出来,她可能用的都是中间那个频率,我用的是她两头。”
但舒淇清楚地知道生活中的自己远离着两极—她既不是“纯情的、为爱所困的女孩”,也不是Shirley杨这种“一天到晚在发脾气的女人”。在她的体会中,《寻龙诀》里骂陈坤和黄渤让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去死吧”的戏是她觉得最难的戏份之一,而她不够凶狠的表现以及发声方法,让镜头里走远的黄渤跟陈坤还要不时返回来指点她。“因为我从来不会那么大声骂人的,我自己本身不是这样子的人。”舒淇说,“我觉得骂完一场,都好像可以再吃一顿饭了。”
“你觉得你是更善于撒娇还是发怒,或者说,你更像大女人还是小女人?”
“我自己吗?我不晓得,我自己还好,因为我比较不会生气。我生气不会像Shirley那样子骂人,我是生闷气的那一种。”她说,“我觉得有时候吵架、骂人是挺伤人的事情,所以我通常都会不讲话。如果说真的在讲的时候,你还是要在理嘛。”
“你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智的人吗,其实私底下的你来说?”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独立吧,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解决嘛。”她沉吟了一下说,“所以我觉得,对,相对讲我是会想得比较清楚的那种人,对或错不晓得了,但是就是会思考的人。”
不得不说,如今即便是在爱情小品电影如《落跑吧,爱情》、《剩者为王》里的舒淇,相比早年亦多了一份从容,亦喜亦嗔,都是一个驾轻就熟的自己。
“其实是觉得自己就不再想演那么多悲剧、纠结的电影,我就想要演比较直接,然后开心,happy ending的戏。”舒淇坦陈“自己之后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挑战的角色”,“因为比较纠结,或者是有难度,或者是有压力的那种电影,也演得不少了,所以就根本就不太想把自己投入在一种不开心的情绪里头。”
我相信,所有的任性,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有足够的底气。无可否认,舒淇曾经是演“望断”最传神的女星—那时的每一部戏,她就好像望见了自己的命运一般,那种“美人草”般爱上不该爱之人的悲从心底,和戏交织在一起:《玻璃之城》里,是她终于抬头望见在下面的车里数次望向她的男人,她的手边是数次犹豫没有拨打出去的电话,是从来不曾离手的,他送给自己的,生命线、事业线、爱情线都由她的名字组成的手的石膏像,雨水隔着玻璃窗在她的脸上肆虐,她定定望向黎明的眼神仿佛什么都没有,又仿佛满脸是泪;《天堂口》里,是她躺在床上,张震在她身边坐着,她轻轻地、几乎不为人知地叹了一口气,望向他说:“绕了那么一大圈,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我们留在这里好不好?”他默默地笑一笑,俯身低头吻向她—那是一个缠绵激烈的吻,好像替代了所有他戏里戏外想对她说的话。
其实不那么爱向全世界表达自己,舒淇这种女明星里的少见特质却是一种难得的自知与理智,因为爱情与人生,终究都是冷暖自知的事情。我还没有告诉舒淇,看过她的那么多电影,看过最多遍的却是一部叫做《玻璃樽》的爱情轻喜剧,她在里面饰演那个叫“阿不”的海豚女孩,和成龙搭戏,演技青涩,其中真实可爱的少女韵味却让人永远无法拒绝——直到这次写稿前重温,我才记起里面有任贤齐的身影—时过境迁,昔日与成龙搭戏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足够成为别人电影里“最美的运气”—执导《落跑吧,爱情》的任贤齐这样说,执导《剩者为王》的落落这样说,真人秀节目《燃烧吧,少年》里的少年们也这样说—而舒淇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圈里,我都不听人家讲话,第一反应就会是‘好烦’、‘不要’……现在我也同样觉得,可以吸收到什么,最重要就是他自己的天分,看会不会遇到贵人,还有在这个娱乐圈的抗压性……这些都不是可以教的,我觉得就简简单单、顺其自然吧。”
简简单单、顺其自然,人人关心的她的爱情显然也会是这样。那些年的电影已经翻篇,如今的电影里,有些人至今依然可以搭档演默契动人的对手戏,好比在《聂隐娘》里,但最终她的选择不是张震饰演的表哥田季安,而是“简单”的磨镜少年。
“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她只是送他走了,到了某个地方,她也不一定跟他去。”舒淇说。
人们看她如一代名伶,总要有一点不归感——滚滚红尘,天下奇迹,就不该归属于谁。
但我想大约其实没有人比舒淇更明白:归根到底,世间深情,莫过自知——这个变幻莫测的名利场,是一座与爱情不分伯仲的玻璃之城,在外面看,一切都美得惊人,只有在其中待着的人,才知道有多么千疮百孔,沧海桑田—美不是通往幸福的通途,男人也不是,真正不会如彼岸花凋零的,是那个无论任何经历、方式、他人,都无法磨去的真正的自己,那个自己最喜欢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