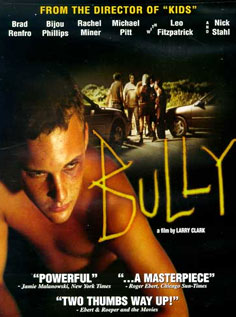《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1969)
轻喜剧风格的西部片。 两位主人公都是反英雄类的典型,是令人愉快的个人主义者。特别是保罗·纽曼,自命不凡,永远乐观,从没杀过人,整天幻想着全世界的银行都已时机成熟待他轻取,实实的一个空想家。他与搭档神枪手罗伯特·雷福德爱着同一个女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打抢或逃亡时还一路诙谐打趣,这与传统西部片里的歹徒绝对两样。 影片温情而饶有趣味,因纽曼和雷福德的表演而大放光芒。两位男星英俊迷人无疑是主要吸引力,但他们确实也得益于编剧威廉·高曼的机智诙谐和导演的超一流水准。该片最终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最佳摄影、最佳音响、最佳音乐项大奖。人们把它推为首席非主流西部片,其实有什么比票房更主流的呢?
《红河》(Red River,1948)
这是一部父子间竞争与反叛的悲剧故事。独断专行的汤姆·当森(约翰·韦恩饰)离开情人来到牧牛乐土德克萨斯,渴望开疆拓土,一展伟业。他收养了从印地安人大屠杀中逃生的男孩儿马修,亲如爱子。数年后,马修长大成人,不再驯服,转而激烈反抗。危机一触即发。 再没什么比父子俩驱赶着浩浩牛群前往异乡一幕更有看头儿了,这经典一幕简直就是场英雄诗史寒冷而艰辛的旅程,外部环境危险丛生,人物内心紧张几至崩溃,有点像《奥德塞》。《红河》几乎囊括了西部片的一切要素:枪战、人潮、偷袭、绞刑、背叛、复仇、情爱、光荣,要论特别点儿的,就算约翰·韦恩精彩绝伦的演技了。如果说韦恩靠《关山飞渡》脱离了低级西部片,那《红河》就让他一举跃为第一票房明星。该片凝固了他的银幕形象:语调暴躁,个性倔强,富于伟大、迷人的男性魅力和内在感召力。
《搜索者》(The Searchers,1956)
约翰·福特的又一杰作。在一次印地安人突袭中,仇恨一切印地安人的退伍老病埃森·爱德华兹(Ethan Edwards)(约翰·韦恩饰)哥嫂被杀,侄女被掠。于是埃森在其兄养子马丁(有印地安人血缘)的陪伴下,开始了搜找侄女的艰辛岁月。数年间,搜索渐渐变成了别具目的的迷狂的举动。侄女已成印地安部落一员,他找她只为杀死她。 福特独具天赋,把个典型的寻仇故事精工细作成关于种族主义和盲目仇恨的深层思考,抓住了一个有着荒谬过去和未卜将来的国家的情绪,影片因之变成了跨越时空意味深远的现代寓言。 该片使韦恩达到表演巅峰,而出色的视觉效果(最后枪战一场也是所有西部片中最佳一幕)也成为后辈楷模。要是谁说还有比它更绝的影片,那就看埃森着名的反诘:“等着那天吧!”
《关山飞渡》(又名《驿车》)(Stagecoach,1939)
早期西部片的突出之作,耗资甚巨,风格新颖。该片开启了约翰·福特与约翰·韦恩富于传奇色彩的合作,也给其后所有西部片划定了优劣准则。 福特以“历险+社会反省”的模式创造了现代西部片。福特透出这样一个信念:在所有荒蛮地带(物质的与精神的),拯救都是可能的。正是这辆驿车表达出美国充满希望的美好前景。当韦恩和特里沃一骑绝尘,奔向灿烂晚霞,我们的心已与之紧紧相随。 影片为福特打定了杰出导演的地位,并帮约翰·韦恩挣脱了低级西部片无穷无尽的的泥潭,建立了具有超凡魅力的银幕形象。它还成功运用了光线的明暗配合和低矮顶棚的效果,这一手法在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导演《公民凯恩》(1941)时大为借鉴。 “驿车”模式后来被多次沿用(如影片《大饭店》(Hotel)、《机场》(Airport)等等),用得多了当然会不以为意,可是你得明白,早在1939年西部片就能有此突破是多么了不起。
《杀无赦》(Unforgiven,1992)
杀人越货臭名远扬的暴徒威廉·芒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饰)结婚生子后弃恶从善,一心一意要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不久妻亡家败,为了照顾年幼的子女,告别枪手生涯11年的芒尼接受了小镇被毁容妓女追杀凶手的赏金,为讨回妓女尊严而战,重涉江湖杀戮。 这是部格调低沉的西部片,包括语调、画面以及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作为西部史诗剧的新生代,该片向西部片有关道德的陈词滥调发起了挑战,并试图从各个角度突破老式西部片造就的神话。后者一举一动皆为增加英雄人物的神话色彩,而伊斯特伍德则更趋于现实主义:展示累累伤疤,写实化杀人场面,主人公还被女人咒骂,这在以往西部片中极其少见,几乎所有主人公都以之为耻,就像不让他们开枪骑马一样。你能想象约翰·韦恩被谁咬了一口而绝无反击吗?
该片剧本早在1976年即告完成。伊斯特伍德拿到拍摄权后按兵不动,一直等到自己老得足以与剧中角色相配才开拍。当然这部片子值得这么等:影片还获得了奥斯卡九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辑四项大奖。
《野帮伙》(The Wild Bunch,1969)
人们都说本片是银幕暴力扩张的里程碑,这话不免眼光短浅。派金帕把白热化的血腥枪战拍成了图解化的暴力,一幅幅曼妙写意,精美绝伦有如芭蕾,绝对是大师手笔。派金帕的慢镜头和鲁·隆巴多(Lou Lombardo)的剪辑被奉为西部片的里程碑之作,派金帕也由此超越了传统的西部片,步入具有纯粹电影冲击力的慢镜头王国。
不仅如此,该片故事也很吸引人,是“动荡岁月里一群坏男人的故事”。1913年,德克萨斯一个败落的抢劫团伙准备最后再干一次即告散伙。匪首派克(威廉·霍尔登饰)曾名震遐迩,不过这次他们遭遇埋伏,被彻底击溃。派金帕的影片既像史诗,又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故事:出卖忠诚,负隅顽抗,为扞卫名誉(尽管已日渐衰败)战斗到底。
派氏电影很多都以男性群体为表现主体。该片中派克与好友由友至敌,这种友情的演绎让该片锦上添花。《野帮伙》不应被严格定义为暴力片,它构划出一种神话般的均衡,充溢着丰富的性格、对话,以及对穷途末路的违法传统苦乐参半的反讽,堪称杰作。
《温彻斯特,73年》 (Winchester `73 ,1950)
《温彻斯特,73年》是50年代由詹姆士·斯图尔特与安东尼·曼合作颇负盛名的5部西部片中最棒的一部(其余4部依次是《蜿蜒的河》(Bend of the River)、《来自莱若迈的男人》(The Man From Laramie)、《赤裸裸的刺激》(The Naked Spur)、《远乡》(The Far Country),被认为是刺激西部片票房回升的主要功臣。该片还开了一道历史的先河:由该片起,明星们不再靠领取薪水(尽管高得让人咋舌)过活,而趋于影片票房利润分成。这招儿让詹姆士·斯图尔特挣了大钱,也永远地改变了好莱坞的交易方式。 影片本身也令人印象深刻。安东尼·曼手法尖锐而富于心理剖析,刻画了一位陷入扑朔迷离中的强悍男人。牛仔林·麦克达姆(詹姆士·斯图尔特饰)为找回一支宝贵的温彻斯特1873年造连发步枪,一路追踪,由此开始了一连串的历险。最后一幕极其壮观:悬崖绝壁间,两人拔枪对射,壮阔山色也每每令人流连不已。《温彻斯特,73年》使詹姆士·斯图尔特名列十大票房榜,而此前电影公司竟怀疑他的表演才能。就像真正的1873年造温彻斯特步枪,《温彻斯特,73年》也是“千年之唯一”。
《黄金三镖客》(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 ,1967)
意大利导演塞吉尔·里昂作品风格独特,号称“意大利面式西部片”。该片是其“美元”系列的巅峰之作,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三个打劫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善)、李·范·克里夫(恶)、丑:埃里·沃里奇(丑)为攫取联邦政府的一车黄金而结成相互背叛的同盟的故事。典型的里昂式影片陷入沉思的回顾,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气势恢弘的暴力画面,还有埃尼奥·莫里科(Ennio Morricone )令人无法忘怀的配乐。 里昂的“意大利面”先编出三个个性迥异的人物作原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当然是主料,但埃里·沃里奇令“丑”这一角色意蕴丰富,他与伊斯特伍德怪异的伙伴关系是片中焦点),然后加上超现实主义的调味酱猛搅,叙述被切成薄片像掷骰子般甩出。最后,还撒上了香喷喷的异国风情调料。比如配音,里昂本身就对英语不感兴趣,片中掺杂了大量非英语语言:“丑”埃里·沃里奇又叫Tuco Benedito Pacifico Juan Maria Ramirez;比如配乐,埃里奥·莫里斯以随意爆发的古怪叫喊合成配乐,极其滑稽,也极其令人惊异。当然还有着名的墓地决战一场戏里,脸、枪、手、眼,镜头急速闪回,将紧张推向瑰丽的高潮。 总之,《善恶丑》与迷幻气氛达到顶峰的60年代十分相称。
《枪手》(The Gunfighter,1950)
格里高利·派克把反英雄的主角,疲惫不堪的快枪手吉米·林戈(Jimmy Ring)摆脱声名的渴望与挣扎演得出神入化,深入人心。上了年纪的吉米·林戈仍是西部声名赫赫的第一快枪手,到处流传着他的传奇故事。但他已厌倦这一切,只想避开声名之累,与多年未见的妻儿安度余生。然而他所到之处,总有一帮自负的小字辈尾随而至,死缠着要跟他比个高下。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既已走出,便无归途。 不知是否出于虚情假意,人们很久以后才开始承认该片的不凡之处。这也在情理之中,50年代的观众还无法接受我们今天看来很明白的事实:好名声固然响亮,坏名声更惹人注目,君不见莫尼卡·莱温斯基,她一心向往的不就是做个普通人吗?让我们回味一下林戈最着名的一句话:“我每到一地都要碰到你这样自负的家伙,我能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向你的朋友大肆炫耀吗?”不管你是不是牛仔,吉米·林戈都能感知你的痛苦。
《正午》(High Noon,1952)
小镇警长威尔·凯恩(贾利·古柏饰)的宿敌在其婚礼正午时分前来了断恩怨,而这一天正是凯恩准备退职与新娘另辟新生活之日。当他被不领情的小镇抛弃(甚至新婚妻子也不理解和支持他)而不得不独撑危局时,他必须在自我的正义感与对新娘(一个和平主义者)的忠诚之间作出决断。正午渐近,孤独的凯恩走在光秃秃的大街上,我们无法忘却这一幕,它让人膝头发软。
《正午》捕捉到了一切经典西部片的要素:独撑危局的英雄,紧张的结局,富于社会意义的主题:简单,直率,且具有毁灭性。 该片编剧卡尔·弗曼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名列好莱坞黑名单并被捕,他将自身的紧张感深深溶入戏中。
许多人都认为该片是对麦卡锡主义消极容忍的讽喻式反映,是好莱坞受迫害的艺术家们“独撑危局”的现代寓言。强烈的政治意味使其作为第一部“成人”西部片而载入史册。